国学概论教案
第一课时:从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反思说起
教学目标:1.了解国学,接受国学,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国学的兴起建立起清晰的认知。
2. 在与西学的比较中,辨别国学特点,以及了解提倡国学研究在新时代的现实意义。
3. 树立正确的国学学习观。
主要研讨重点:国学何以重提?
设计思想:国学话题比较具有学术性,可以从身边的事情谈起。我们可以从文化现象中去总结一些问题,从而提出这一话题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意义。社团起始课,初次碰到这么学术的问题,可以以教师的讲授为主,主要为达到一个吸引学生兴趣的目的,让他们有参与其中的强烈意识与积极性。
一、导入
1.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
时尚的穿着(附图)
时尚的表达
沉重的反差(附图)
沉重的新闻(附图、文)
2.对问题原因的探讨:
商品经济的影响——金钱万能
官本位的影响——权力万能
传统文化失落的影响——无耻万能
3.专家对传统文化失落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称:
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漠视文化本根做法的后遗症将显得日益严重,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4.明确“国学”重新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反思
(一)先贤对于中国衰落之原因的认识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彻底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同时也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观念上和结构上的严重问题。
因此,当时一些思想家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弱点,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在洋务派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人伦道德、社会习俗等方面不仅不可改变,而且其传统远优于西方,因此也不必改变。于是,他们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把中国传统的“治统”和“道统”归之于“体”,把西方科技、器物文化归之于“用”,并提出了“中体西用” 的根本方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把洋务派三十年来从事洋务运动的心血毁于一旦,从而也就使人们对洋务派所遵循的“中体西用”的方针提出了疑问。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关注的是对封建政体的局部改良抑或根本的改变。近代中国人的学习西方文化,由此而深入了一个层次。
戊戌变法的惨败和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的现实,迫使人们进一步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次的“道统”问题。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检讨,其中主要集中在经过宋明理学系统化了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与封建伦理纲常观念、道德规范等方面。同时,则开展了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学术风气以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等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一面高举“德先生”(Democratic,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 ,科学)两面大旗,一面则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和彻底粉碎“吃人的旧礼教”,把批判传统文化和接纳西方文化的社会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自此以后,确定了本世纪中国文化结构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基本格局。这不仅是指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变,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各种观念上的变更,尤其是传统价值观念上的变更。当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欧美是时代的理想国,西方文明尽善尽美,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一应以欧美为榜样。
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对世界各国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西方文明尽善尽美的幻觉,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其中,如1920年初梁启超旅欧回来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和1921年出版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两部著作。
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也开始把目光移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研究。1922年 1月南京东南大学由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创办了《学衡》杂志,1923年 1月北京北京大学又由胡适等创办了《国学季刊》杂志等。在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了一股以新的学术眼光和方法研究传统学术文化的潮流。
在一些著名学府中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办起了各种以研究传统学术文化为主的专门性学术刊物。其中如,1919年 3月由北京大学文科编辑出版的《国故月刊》,大概是最早的一种。著名经学家刘师培在为此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公开声明该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效法西方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取向。
(二)先贤对于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先生同时也是“整理国故”的大力提倡者,然而他的“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打鬼”、“捉妖”。他说:
“你且道清醒白醒的胡适之却为什么要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我披胆沥肝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
以上表白,说明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昌明国粹”,而是为了揭示和批判传统文化中“吃人”、“迷人”、“害人”的东西。他曾明确表示“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1933年底当时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中声称: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反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
理由有二:一是“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二是“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他还特别伸言:
“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讲究。在西洋文化里面,也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之,在中国的文化里未必能找出西洋的好处。”
这些申述,显然是极其片面的。然而,“全盘西化”口号提出后,一时附和者却甚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
但在这一时期也仍然出现过比较理性的声音。
1935年初,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而为了“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其基本的要求和办法是:
“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只有“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
在这次讨论中,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化”不等于“欧化”或“西化”。如说:“‘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他们认为,就中国的现代化来讲,既要“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同时也需“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以上这些观点和想法,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但中国近代史的无情事实是:在社会具体改革的实践上,在文化建构的总趋势上,一直是“西化”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传统文化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健康的发展,相反却经常成为受批判的对象。提倡传统文化常常被扣上“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科学客观的历史总结与现代诠释。
应当说,在以往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化走以西方化为主的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的审视与反思一下以往这个世纪中国文化所走过的道路,则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认识上和结构上的偏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严重失衡。而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从近代实行新式学校教育以来,我们的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仿照欧美(以后又是苏联)模式,而课程内容也以西方文化为主,在教育方法上也是以西方为主。反之,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几乎全被摈弃,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内容更是少得屈指可数。
(三)传统文化研究的思想障碍
至今,在不少中国人的思想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两个解不开的情结,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与科学的成分,乃至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与民主、科学相排斥的,无法相容的。
毫无疑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找不到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和自由、平等观念的。事实上,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也并非古已有之的,而是在社会发展到以工商资本为主要形态以后,并且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才发展起来的。
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并非古已有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西方传统文化毫无渊源关系。众所周知,西方近代文化发端于十四至十六世纪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亦即是罗马、希腊古典文化的复兴。
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正是西方实证科学最为兴旺的时期,理性至上与逻辑推理,实证至上与普遍有效等被视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凡与此不一致者,则被斥之为非理性的、非科学的,甚至是愚昧落后的、神秘主义的,应当被淘汰的。
现在,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发现实证科学的方法远不是完满的,更不是唯一的。许多科学家在研究中碰到用实证科学方法无法证明和解释的问题时,正在越来越多地到东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混沌的理论与方法中去寻求解答,并且取得了相当可喜和可观的成果。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在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
“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当作为胚胎学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由于在西方科学的机械论理想(以服从普适定律的惯性物质的思想为中心)中无法找到适合于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而感到失望时,他先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然后也转向了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便倾其毕生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科技和文明。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中国的独一无二的资料,并且是反映我们自己科学传统的文化特色与不足之处的宝贵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波尔(NielsHenrikDavid Bohr),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至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这个接近也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和胚胎学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直接面对‘自然规律’的含义问题。”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既有时间(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有类型上的差异,而其中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根本的。当我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最主要的是应当注意其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其间由此而形成的各自不同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以推进全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共同繁荣和发展。
在中国,由于单纯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彻底失败,维新变法的失败,乃至辛亥革命果实的被篡夺等等,更增进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上落后的想法。这也就是在以往一个世纪中为什么会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强烈批判和否定倾向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境况不断改善,国力的强盛,促使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思和自觉,并开始恢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这正是我们所以提出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根据。
对待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因为,这种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自地区、民族、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凝聚着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族的特有性格和精神风貌(诸如生活习俗、礼仪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因而它也就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今天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
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的。从古到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这种交流总是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中与己有益的营养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因此,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主体意识是不能没有的,否则出主而入奴,势将沦为它种文化的附庸。
(四)新世纪传统文化发展的展望
本世纪上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曾引起世界许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内涵与特质进行思考,这些学者大都注意到西方文化结构中唯科学主义、唯功利主义的偏颇。而本世纪下半个世纪,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严重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开发,无节制的浪费性消费,造成了地球生态的严重失衡和生活环境的日益恶劣。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和生物过程的随意干预,已种下了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一切都引起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深思。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都有不少学者反复提倡“新人文主义”,以期摆脱人类日益沦为机器、物欲奴隶的困境,以期找回失落了的人性、自我。而当他们倡导“人文主义”时,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传统文化。
在中国,经过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新的认识与重视。人们对八十年代新一度的西方文化冲击波也进行了反思。因此,从八十年代末起,社会和学者们又都对传统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国学”、“汉学”等概念重新被提出和讨论,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近年人民大学更是成立了国学院,以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表现为注重人生伦理价值与艺术品味,注重人生的自我修养与精神生活。
本世纪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可以说是对科学技术的绝对崇拜。
其次,传统文化中那些模糊、混沌的理论与方法具有独特的价值。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全体大用(部分反映全体)的观念,整体把握、普遍联系的辨证思维方法等,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很有补益的。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中西哲学的不同,他是这样说的:
“外国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譬如古代,希腊、印度的哲学,都以地火水风为万物的原始。外国哲学,注重物质,所以很精的(指分析精细、精确)。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如老子、孔子,也着重在人事,于物质是很疏的。人事原是幻变不定的,中国哲学从人事发出,所以有应变的长处,但是短处却在不甚确实。”
章太炎的论述虽然十分简略,也很平常,但他确实非常准确地指出了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
西方哲学从静态物质发生,其观察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就以注重静态分析为主;中国哲学从动态人事发生,其观察方法和思维方式也以注重动态关系为主。静态分析,其注意处为各个部分和细节;动态关系,其注意处为整体全局和大概。西方人习惯于分别计较,物是物,心是心,分析物时可以与心无关,分析心时可以与物无关;中国人习惯于关联思考,心不离物,物不离心,也就是说,分析物时不能离开心,分析心时也不能离开物。
因此,如果采用西方的那一套观念和方法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就好比是用实验室的观念和方法去诠释原来建立在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基础上的理论或问题,常常会是文不对题、似是而非、失其原意的。
所以,必须采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研究方法”,即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 “体悟”的基础上,能够从整体上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征的方法;能够在把握这种整体精神和特征的基础上,去诠释各个分部精神和特色的研究方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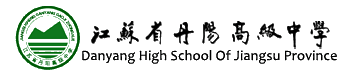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 32118102000018号 省丹中信息网络中心制作维护(建议1024*768+IE7.0以上)
苏公网安备 32118102000018号 省丹中信息网络中心制作维护(建议1024*768+IE7.0以上)